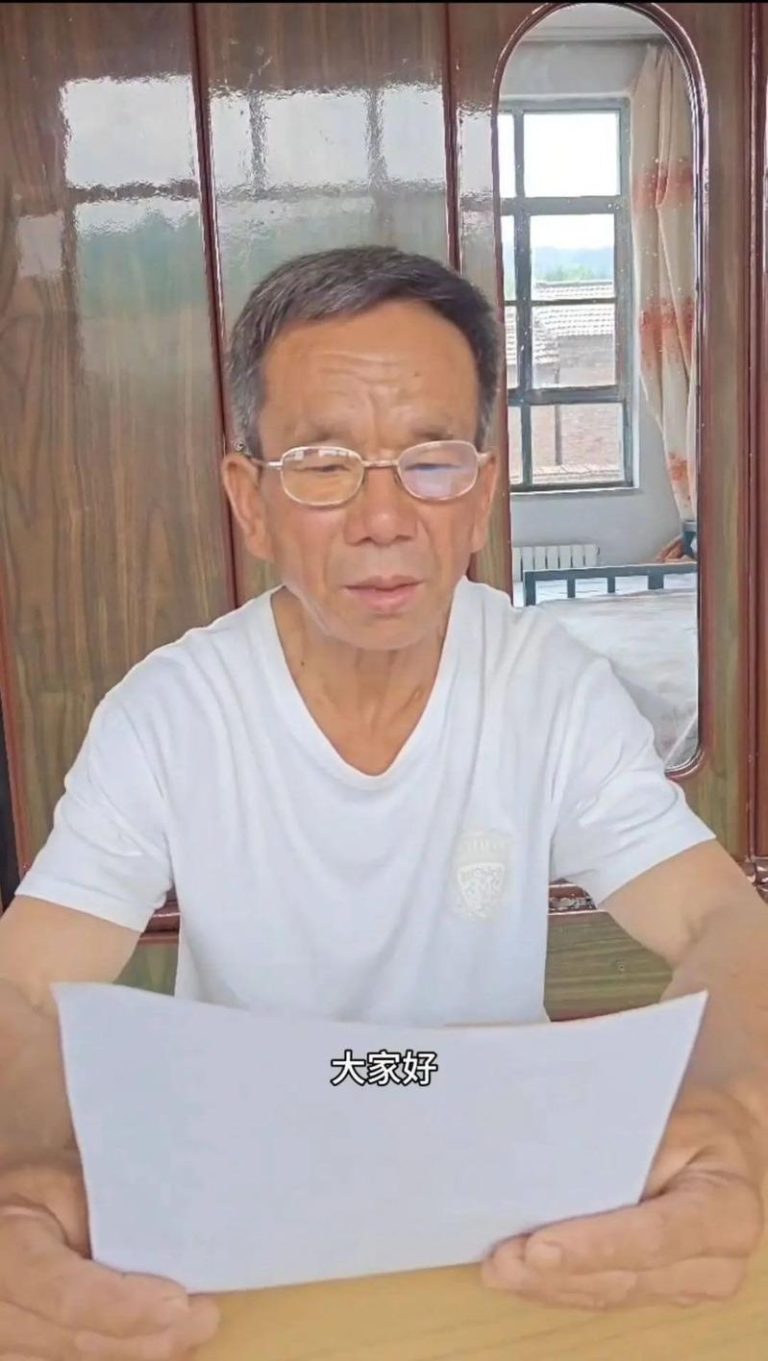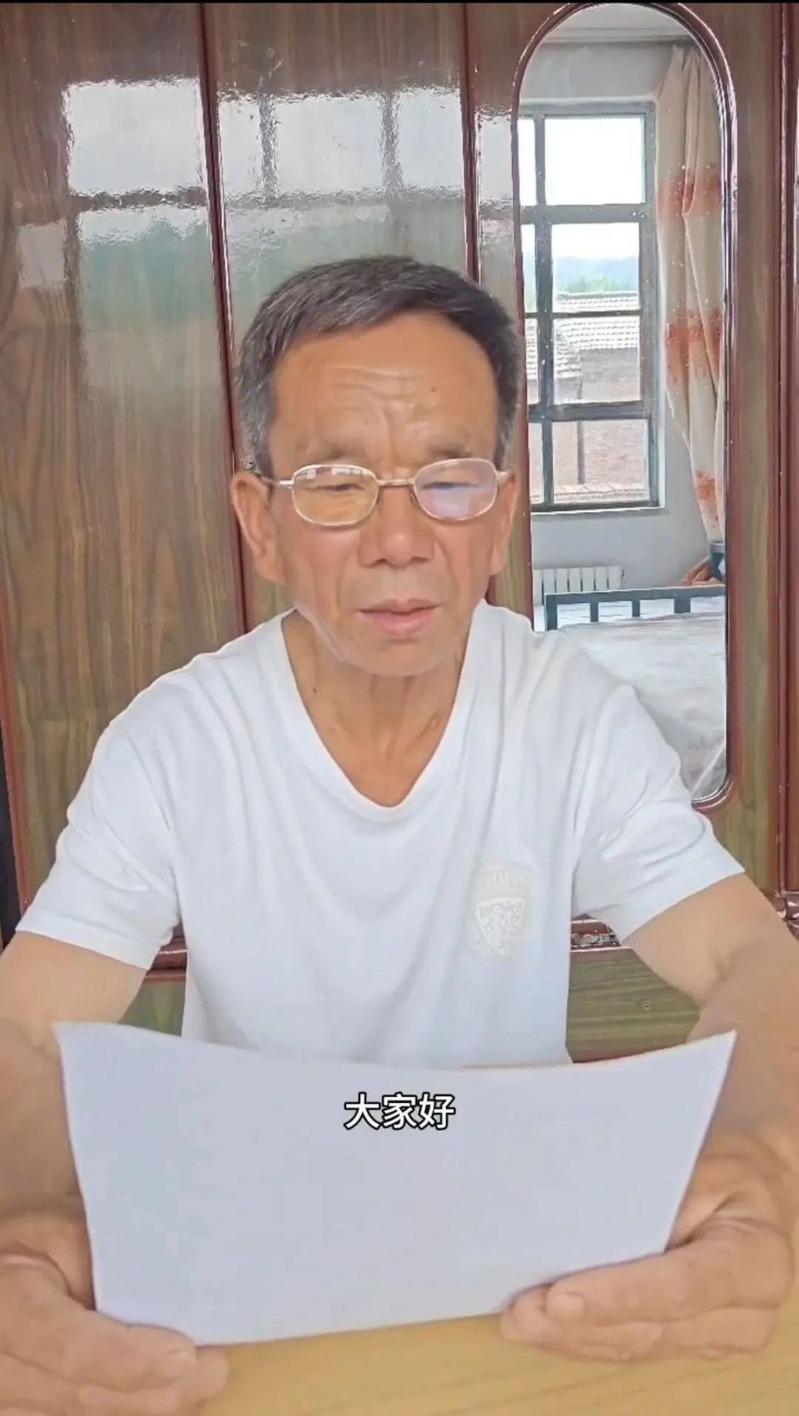
「等哪天我扛不动水泥了,就回村里挨着那堆土躺下,没准那时候,我再叫妈妈,她就能听见了。」一篇800多字的作文,写出了对母亲的思念,也让山西太原市山村里的农民工安三山一夕暴红。但对他来说,语言的能力虽能超越一切,但想靠写作改善生活,那是不切实际的白日梦。
对身为农民工的安三山来说,要想赚个1000元人民币(约140美元),得在逼近40℃的日头天站上3天,搬2万块砖,铲好几吨重的沙子和水泥。所以,当他听到写一篇作文就能拿到这些钱时,他没有丝毫犹豫,「一辈子都没碰到过这种好事」。

★用高考题 赢得1000元现金
新京报报导,让安三山一夕暴红的那场街头挑战,其实是一场巧遇。在前一天,安三山干了一趟300元的活儿,晚上睡得很差,隔天他睁开眼,已经是早上5时40分,平常这时候他早就吃完早餐,坐上去工地的车了。但也因此,安三山在路上遇到了正在做街头挑战的女孩,参加者可以选择直接拿走100元离开,或是用历届高考题目写一篇作文,就可以获得1000元现金。
有着高中毕业学历的安三山虽然不懂这些互联网上的花招,但他觉得划算,决定「挑战一下」。在拿到「我的母亲」这个题目时,66岁的他脸上看不出情绪波动,但他在作文开头写下:「重温母亲的回忆,我思绪万千」。安三山从随身带的红布袋里掏出老花眼镜戴上,在空无一人的餐馆里写作,没有打草稿,文本像是从笔尖流淌出来一样,完成了一篇800多字的作文。
他写「天不亮就起,摸着黑才歇」的母亲,写她洗得发白、补丁叠着补丁的衣裳。他写家里「那口烧柴火的大铁锅,死沉死沉」,但母亲瘦小的身子总能稳稳端起来。有那么一、两次,安三山在工地上累得擡不起砖时,母亲擡大铁锅的身影就出现在眼前,于是他咬紧牙,又能挤出些力气—「母亲没享过福,可她教会我的,就是这骨子里的硬气和对家的担当」、「我得把您撑起来的这个家,接着撑下去,撑稳当」。
他写母亲「心善,能容人,跟邻里没红过脸。」在工地,安三山因为个子矮,被工友叫「武大郎」,但他总是笑笑。

★创作金句 看哭无数网友
母亲曾是他最大的依靠。八个孩子里,只有他和二哥上学,一个铅笔掰成两半用。家里供不起后,母亲做主让二哥回家,他回到了学校。母亲借钱买来白布,踩一整夜缝纫机为他赶制白衬衫。晚上,他点着煤油灯看书,两个鼻孔熏成黑色,睡醒后,母亲已经为他擦去。米少得只能熬汤时,母亲总会悄悄给他留一碗稠的。
生病的那两年,母亲整天围在床前照顾他,给他包最香的饺子,搀着他在院子里散心。自己病好了,母亲却累倒。母亲50岁出头就走了,留给了他这辈子最难以释怀的遗憾。
「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,黄了又青,就像我的念想一样,一年年总也断不了。」安三山写下这句最为人传诵的文本。当他的文章被传到网上时,「看哭了」无数网友,一夜之间抖音、快手上全是他,还上了大大小小的新闻媒体,甚至有人建议把作文纳入中小学课本。网络上更冒出不少素未谋面的「儿女」,逐字拆解他的写作技巧;也有人一本正经地分析,试图证明作文不是他写的。
后来安三山的作文登上了报纸,连村里不识字的老农都听孩子念过。一拨又一拨的人登门拜访太原这个偏远的山村,路边停满了车,一度堵得「迈不开腿」,全是来看「作文大爷」的。他不知如何应对,只能不断重复:「我就是个农民。」
报导指出,那几天,安三山家里的小院里外挤满了人,家里杯子不够,罐头瓶都派上了用场。围观者举着手机,试图在他身上找到一些独特之处,但大多失望而归—安三山太普通了,甚至有些不起眼。
他不高,身材精瘦,长一截的大号T恤让他显得更加瘦小;他也不像视频里那样白,皮肤黑黄,脸上皱纹就像西北的山,沟壑分明;那双写出「我的母亲」的手也和别的农民工没什么两样,指节粗大,因为被砸伤太多次,一根小指朝外翻着。
来访者很快发现,安三山不是那种在镜头前事事配合的老汉。他谨慎地表达,带着很强的边界感。「在村里到处问」的做法让他生厌,「我家的事就问我不行吗?」关于作文是怎么构思的,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他欣然作答;但若有人问母亲怎么去世的,埋在哪,家里人都是做什么的,他沉默以对。事实上,几乎每个到访者都曾被他拒绝过,他不断强调农民的本分,「不想风风火火」。
报导称,作文火了之后,他总让儿子帮忙点开抖音的评论区,戴着老花眼镜一条条翻阅。安三山声称专看「不好的」,他不喜欢评论里夸他「像作家」的说法,那些评价「我的母亲」文本干净、情感真挚倒是能让他微微点头。

★写作改善生活 他斥瞎想
他抓起儿子不要的本子抄写评论,并在扉页上记下了第一条:「知识分子的知识,应该用于理解和帮助,而非揣测和计算。」右下角,是评论者的暱称。
有来访者说,安三山戴上老花眼镜时,像个知识分子,对此他反应激烈。当被问到「有没有想通过读书和写作改善生活?」他也十分恼火:「那是瞎想、幻想、白日梦」、「不吃苦,不受罪,还能改善生活了?」
作文火了后,很多人说他像电视剧「平凡的世界」里的男主角孙少平。安三山也在下雨天没法出工的时候,到书店看过这部小说,但只是翻翻,「没看几页,因为没时间。」
他不是没有过别的可能。1978年,他是郑家庄村少数能念到高中的年轻人,校长和老师不止一次挽留他任教,他都因为家里缺劳动力,还有薪水微薄拒绝。他顺利通过征兵体检,分到了青海天峻县的铁道兵部队。在连队,他仍然是「高材生」。当义务兵役期满,他又一次被挽留,但他再次选择离开,因为听说「复原回地方好找工作」。
报导指出,安三山后来到古交的一个机械化砖厂当工人,负责把滚烫的红砖从轨道车上卸下,每天工作九个小时。如果他一直干下去,现今早已是退休工人的身分。但没过几年他生了场大病,卧床两年,等身体康复了,那条想像中通往「公家人」的狭窄信道,在他眼前彻底关闭了。

★半生经历 让他学会认命
「情况就是那个情况,你后悔也不顶用。」他说起这些往事,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希望在破灭之后,成了他嘴里的「瞎想」。半辈子的经历让他学会了认命,对待世界,他回以深深的沉默。
病倒的那两年,安三山的身体被困在炕上,只能翻来覆去地看那几本仅有的书,在笔记本上抄下能触动他的字句。偶尔精神好时,写写日记,「我认为语言的能力超越一切,它胜过了金钱、力气、权力,这一切一切都需要语言穿过」、「星星向往月亮,我在寻觅知音」,笔迹时而工整,时而潦草。
但当生存的力气回来时,那本日记和那段试图与自己对话的脆弱时光,迅速显得「不切实际」。报导称,在一次整理少得可怜的家当时,他把日记本和一堆旧报纸一起卖了废品;当年看过的书,如今「糊了窗户和柜子」,那是它仅剩的价值。
●文中「妈妈」压在心底30多年 冲破了沉默
在大部分时候,安三山的情绪表达,只存在于他那用土墙筑成的堡垒里。他喜欢给家里的各种对象题字,房前架电线和自来水管的木棍上,贴着毛笔字写的「生活之源」,原本那是「生命之源」,他斟酌后,觉得「生活的内涵比生命更大」,于是换掉。水井的挡盖上曾写过「井水长流」、「井泉长流」,但都不如现在的「细水长流」,「也形容生活嘛」。
他喜欢留意细节,有时会突然指着院子里的一株草,让孩子用手机搜名字,然后「用心记在脑子里」。被问到是不是有随手记的习惯,他摆摆手,「哪还能经常拿个本?那就不是劳动人民了。还用拿笔?那成了啥了。」
安三山得到的,除了那实实在在的1000元,从附近市场买了十几斤猪肉带回家,还有受媒体的邀请生平第一次去了北京,似乎再没有别的。
有人建议他开直播,继续写文章。他说:「我就是个受苦人。」他用农民歌手大衣哥当例子:「被人家在村里又围又堵又弄,那叫生活了?我宁愿不要那个钱财。」妻子也有顾虑,见到有人拍照就阻拦,「不要拍。要是发出去,我儿子以后怎么娶媳妇。」
报导指出,在网络上的热闹渐渐平息之后,安三山脱下那件大号T恤和皮鞋,又换上迷彩服,还有儿子不穿了的球鞋。早晨5时,他站在院子里打量老屋的墙面,开始和水泥。
修整老房子的想法早就有了。安三山想给墙抹层灰,装个吊顶,地面铺上水泥。这样等亲戚来时,家里也有住的地方。「房子是人的头脸」,他受了大半辈子苦,也想证明自己「算是活出来了」。
在儿子的记忆里,父亲总是催家人「快点」,不但赶着工期,也追着生活的节奏。但此刻的安三山却细致地打磨墙面,这次儿子当小工,他当大工。他有一套自己的标准:墙要修得平整,说话要恰当,形象要干净。更重要的是农民要守本分,劳动是美德,沉默是金。
大部分时间,院子里只有安三山劈砖发出的声响。这幢老房年久失修,墙上有十多个缺口,在抹灰前,要先用砖补平。安三山举起斧头把砖敲打成想要的形状,塞进缝隙。在这个院子里,子女也继承了他的沉默,面对来者的提问,他们总会瞥向父亲,客气地摆手婉拒。
寡言的安三山在「我的母亲」文章最后写着:「我已经当了爸爸,也已经当了爷爷,但我已经30多年没叫过妈妈了。我想着,等哪天我扛不动水泥了,就回村里挨着那堆土躺下,没准那时候我再叫妈妈,她就能听见了。」文中的「母亲」换成了「妈妈」,这个压在心底30多年的称呼冲破了沉默,或许也就是他最深沉的情绪表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