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「你不是懒,只是能量太低」,这句话成为许多人的救赎。这些年轻人不喜社交,用「最低耗能」与无处不卷的世界搏斗,试图在主流期望与个体本能之间找到平衡点。
近两年,互联网上一批年轻人被确诊为「低能量」,在多数人陷入疲乏与困倦的夜里,他们开始一批批苏醒。有人的外卖刚到门口,开始第一顿「早餐」;有人在手机反射的冷光里,与敌人殊死搏斗;还有人准备骑上电动车,去5公里外为自己补给一瓶冰镇可乐。在崇尚高能量的优绩世界里,低能量年轻人努力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「微活」之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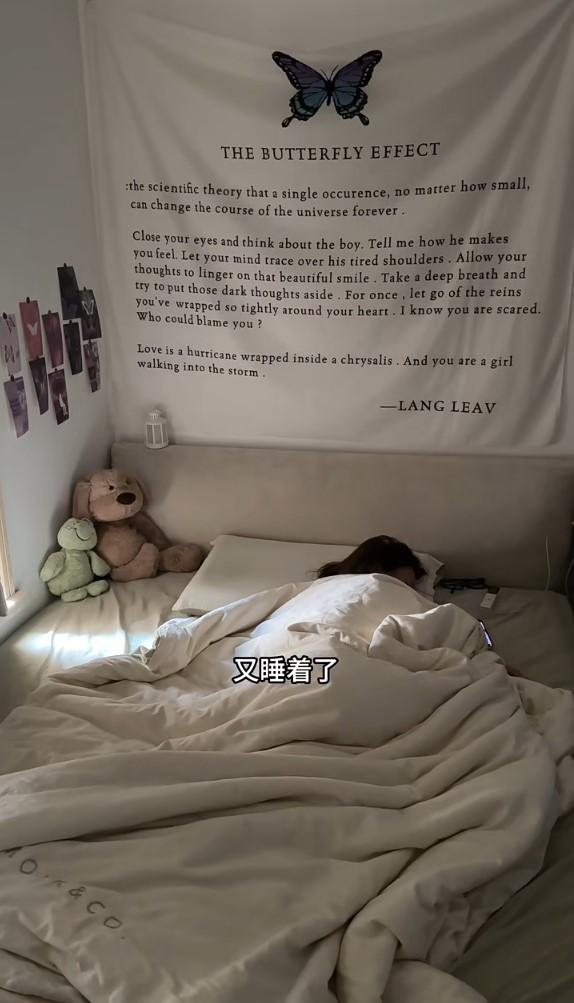
★生活行动力 几乎停滞
「每日人物」报导,近年来,在社交平台上,记录低能量生活的Vlog开始走红,这些人精力匮乏、行动力近乎停滞,拆快递、洗澡都需要心理建设,影片主要是在舒适的房间里睡觉、刷手机和吃饭,许多人在评论区惊呼:「震惊,我的生活视频无意流出。」也有愈来愈多的年轻人开始主动认领低能量的身分。
低能量是「懒病」吗?「你不是懒,只是能量太低」,这句话成为许多人的救赎。谷谷(化名)的低能量,源于一次次艰难的起床,她是标准的「夜行动物」,无论是熬夜看剧的满足感,还是午夜迸发的创作欲,许多幸福感都发生在夜晚。疫情居家上网课的日子,每天早课签到后,她把电脑搁一边,回被窝边睡边听;到了半夜,她精神抖擞,开始在房间活动。这种日夜颠倒的自由,像是在夜里偷来了一切。
低能量常常被跟「内向」挂钩,谷谷说,「我可能看到老师或领导,就假装看不见,或者换个方向走」。父母希望她能像其他外向的孩子一样,会说话、懂应酬,于是她硬着头皮模仿,明明不喜欢社交,却要在场合里说些带动气氛的话;明明不喜欢虚假的寒暄,也要赞美领导同事。她像是揣着两副面孔:社会化让她能体面地应对周围的期待,外界对她印象不错;骨子里却喜欢往边缘站,往角落躲。
陈映(化名)也是低能量一族,当公司组织去沙漠团建,同事们在无数个打卡拍照点兴致勃勃,她却藏身在一个红色遮阳伞下扮「蛐蛐」。对他来说,「团建不是放松,真正的放松是躺在床上」。
「社会化」与自我的冲突,是「低能量」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遍困境—他们需要融入,但又渴望保持真实的自我,这是一种在「主流期望」与「个体本能」之间的拉锯。

★又淡又佛 过一天算一天
王阳(化名)无论生理或精神状态都非常低能量,他总想藏在黑暗里,朝东的卧室他安了两层窗帘,全拉上可以不见天日。他集内向与宅为一体,从小到大,他得到父母最多的评价就是「啥也不想」。他较少筹划未来,日子过一天是一天,「说好听是又淡又佛,不好听就是废物」。
低能量这个梗一出,他200%认为自己就是。作为一名程序员,王阳的轨迹90% 以上是从家到公司。「我的生活,没有太多的波澜,也没有太多的惊喜。它就像一条笔直的、没有尽头的仓鼠跑的那个圆轨道,我只是在上面,日复一日像个仓鼠一样跑,就能活着。」
低能量的生活,常常被一个个连贯却又分散的充电时刻所串联。当能量耗尽时,他们便迫不及待地遁入精神防空洞里充电。
为什么选择「困」在家里?陈映说,家里没有他人的目光。电量耗尽之际,她会一直待在床上,偶尔起身调一杯酒,在微醺中沉沉睡去。醒来,再来一杯,如此循环往覆,直至凌晨。毕业五年,陈映已经换了六份工作,她一直在逃窜:从枣庄到济南,再到北京、天津,无论在什么地方,她都过着一种低能量的生活。

★表面疏离 内心盼被关注
但表面上寡淡疏离,陈映内心深处同样有着被关注、被看见的需求。曾有一个夜晚,陈映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,迫切需要与人交流,社交软件上,一个男生提出见面。然而,一想到要洗头、化妆、换衣服,更要察言观色地回应别人,她立刻打消了念头。
彭聪(化名)专门设置了「充电日」。这天来临前,她会先跟同事、家人预告将去旅行,信号会不好。而「充电日」白天的日程主要是睡觉,一直到了晚上6、7点醒来后,她要做一点心理建设才能打开卧室,她的第一关是门外等待侍奉的五只猫,这是能量消耗的第一环。这些猫没少给她添乱,之所以没想过送牠们走,还是怕麻烦,担心别人照顾不好,「还不如我自己给牠口饭吃」。
「充电日」的吃饭也极其简易,比如馒头配水。她有各种不同口味的馒头,大米的、玉米的、黑豆的,一次进货就是十几袋。蒸锅里扔两个,配着水就是一顿。朋友笑她这是「维持生命体征餐」、「狗都不想吃」,她却觉得刚好—嚼馒头累,点外卖挑选食物更累。
到了凌晨,彭聪会去5公里外的一家零食店买一瓶可乐。来回10公里,一个多小时的行程,还有明确的捕获物,这是她「充电日」的放松旅行。夜晚时谁都没力气琢磨别人的事,这种时候最舒服。
彭聪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电动车,这是低能量的最佳拍档:「开汽车要观察太多情况,电动车就向前骑,还比自行车省力气。」她从不飞车,觉得「太刺激了就很累」,也不听音乐,只慢悠悠地骑,脑子里飘些奇思妙想。到了店里她拿上可乐,不逗留地转身往回骑,怕多待一秒就有人开口搭话,搅了自在。

●低能量族反抗又入世 争取与自我相处
无论是制造「充电日」,还是搭建一个在电量耗尽的时刻可以躲进去的洞穴,低能量也在做另一种形式的努力,从挤压他们休息的大手里,既反抗又入世地争取更多与自我相处的空隙。
低能量的年轻人也各有办法应对高速运转的社会生活。彭聪的职业是律师,一个向来要求「高精力」、「快反应」的行业。同事们大多是能连轴转、高精力的人群,和她这种攒着精力过日子的人,显得格格不入。
但她擅长琢磨省力的方法。与人沟通前,她会先预判对方的思路,「如果不准备,被人问住了,情绪上会受影响,一慌能量就掉了大半」。被老板逼着走不通的路,她不硬扛,悄悄绕去另一条道。
和低能量共存,谷谷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探索。「早起」无疑是她最难跨越的日常「事故」,她常在放任继续睡与对迟到后果的担忧之间徘徊,对她而言,这不只是生理上难以醒来,更像是心理上的暂时性逃避。
念书时,她甚至有一次因为迟到而错过了考试,她鼓起勇气问老师:「我能在办公室再考一次吗?」出乎意料的是,老师同意了。她逐渐意识到,破坏不一定等于失控,关键在于能否承担后果。工作后,迟到成为了她一种微小越界的行为。她会无意识地迟到,并思考审视「准时」的真正意义:如果准时到岗后就开始吃早餐、摸鱼,那么「准时」又有什么意义?一旦迟到,她也会主动弥补:迟到半小时,加班一小时。
她的「人设」逐渐变成:除了爱迟到,其他方面都不错。她觉得这种不完美感也是一种解放。她并不想被「完美」所束缚,反而把这些看似不正面的标签,转化成了与世界相处的缓冲地带。
王阳失业后,变成了更颓废的低能量,他觉得需要出门,但不知道去哪里,常常被没有目标和任务困住。刷短视频看到有人在送外卖,他发现那是一个有明确目的地的任务。于是在一个深夜。他决定试试。第一单他选了熟悉的地方—一个网吧,东西往前台一放,不用敲门不用寒暄,点完「送达」就像游戏里交了任务。
后来跑远些,遇着找不到的楼,他也鼓起勇气问保安。他的世界被更多路线打开,他像打开新游戏一样开始探索家附近的边界。这活儿在他眼里不难,跟打游戏没两样:取餐点是「接任务」,导航是「地图指引」,送到了就是「NPC对话完成」,连2.5元的保险费从第一单里扣,都像游戏里固定扣除的「体力值」。下雨天补贴多一、两元,像触发了「特殊天气buff」,哪怕裤子湿了半截,看着到帐金额多了点,也觉得有成就感。
跑单时他逐渐感觉内心明亮了一些:不用思考人情世故,不用管明天干啥,就盯着眼前这一单。送完七、八单挣够饭钱就可以。虽然接的单量有限,但他发现如果能找到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,他也能走出家门。虽然每次出门后,总能感觉一种拉力,要把他拽回去。
低能量人是警觉的,他们在「反抗」的同时,又融入世界,自我的生活由此产生。
谷谷很容易丧失意义感,当工作中达成绩效目标时,她常觉得「没我也能成」。她看到个人在规范化的社会生产体系里,只是链条上的一环,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。但谷谷逐渐在一些微小的实践里找到了意义—帮室友捅开了下水道,和陌生人因一张照片产生共鸣,关心朋友的工作与生活,甚至在外卖大战中占到了一点「便宜」,也是有成就感的,「低能量动物是弱小的,抢到一点优惠也是有意义的争夺」。
彭聪也在具体的事情里编织意义之网。看漫画解说时,她爱听人讲「火影忍者」里的细节设计,像结印之类的精巧构思,会让她觉得有趣;看电影她会打开上帝视角,观察其中的剧情、运镜设计,这是她为数不多比较耗能的活动。她在不同帐号上发些低能量人的生存攻略,得到过不少关注,也筛选到了志趣相投的同类。
如果让AI老师给低能量上价值,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评论:低能量年轻人的「瘫」不是终点,而是身体发出的生存警报,当功绩将人异化为永远运转的机器,倦怠是灵魂最后的自救。在「低能耗存在学」里,生命价值不再绑定于产出,而在于感受一片落叶的耐心。

